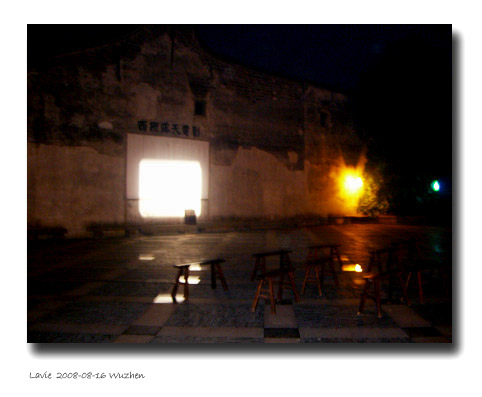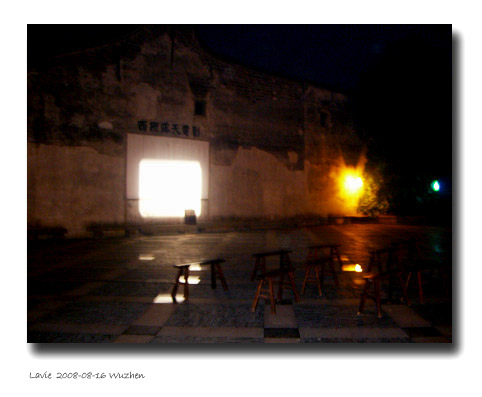[37] 我的低保真记忆冰河 2009-02-04 02:22
看了谭老的文字,倒是勾起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心结,就是对那种夹杂着电流声、爆音、间默、单声道声音的迷恋。我曾经不同程度的表达过这种迷恋,却被多人嘲笑为土包子,就是喜欢稀饭咸菜,无福消受鲍鱼海参。在音乐上我和谭老的口味颇为相似,更注重音乐本身,对于器材的要求不甚了了。甚至可以说,我比他还低档次,他好歹会自己买个好点的声卡和耳机,下载个APE,我却是板载声卡无妨,普通耳机没事,甚至有一个耳机不响了也一样听的津津有味,随便下载个MP3,只要是完整版,就不在乎其中有什么瑕疵。幸好他们不甚听我的音乐收藏,否则恐怕连谭老都会鄙视我到死。
我仔细回味过我的过去,思虑再三之后确定,这是还在襁褓之中,父母带我翻山越岭去兵站看电影留下的后遗症。嗯,那个年代,一场在大风中的露天电影,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,其享受不亚于如今听一场三高演唱会。要知道,天山那么多兵站,轮一次露天电影可不容易啊,三个月一次,还要披星戴月喝西北风,因为辛苦,所以享受。所以我一生中最开始的影像记忆,就是在大风中不断变形的人像,随着风声忽大忽小的配音。《蛇》、《流浪者》、《敖德萨档案》、《最后一颗子弹》、当然还有经典的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。只是那时年纪太小,基本没什么逻辑记忆,故事都是后来再看才有了深刻印象,只是那些伴着我呼呼入睡的配音和风声,却是再也忘不掉了。
“同志们,俄罗斯虽大,也已经无路可退了,背后就是莫斯科,冲啊!”
“天空在颤抖,仿佛空气在燃烧。”“是啊,暴风雨要来了。”
“阿巴拉古,当当当当,阿巴拉古,当当当当……”
(以上内容不妨请阅读者猜一下,都是什么电影里面的。猜中了有奖,我孩子出世之后优先敬赠我签名他的照片,还可附送新鲜优质童子尿)
佛洛依德说一个人在儿时的经历会影响他一生的性格和喜好,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,至少在对声音的癖好上,我是这样的。我可以不在乎那些声音中的不完美,但是只要其中有坚定、勇敢、温柔、阴险……只要有感情在里面,我就会迷恋。
电影配音的问题以后再谈,回到音乐上。由于在新疆长大,没什么条件,所以我的音乐启蒙是非常高档的原生态音乐——人声清唱。内容当然是乱七八糟,从各种红色革命歌曲,到少数民族邻居生子嫁女庆贺中的乱吼。其中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很多湖南民歌(新疆有很多湖南人,我母亲就是,这是自左宗棠进疆后形成的习惯),其悠扬柔美,让人念念不忘,那是充满了山灵水性的南方山歌,让我在干旱荒凉的戈壁上对山清水秀有了一个声音上的认识。当然听的最多的还是少数民族兄弟的新疆民歌,其风格热烈粗犷奔放,加上欢奏的冬不拉、热瓦普琴,让人快乐。不过他们唱起慢歌的时候,也一样非常打动人,因为他们的感情非常真挚,其喜怒哀乐在音乐中都非常直白的表露出来,尽管我不懂他们的语言,我却能明白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。一个典型的例子,是后来我听刘欢的《七十年代生人》中,他演唱的《怀念战友》(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插曲),刘欢的声音非常华美,演唱技巧也很好,高音非常有震撼力。可是我还是觉得原电影里,伴随着都塔尔琴悠然而唱的更好听,因为里面有真正的哀伤。正是这种粗糙却无以伦比的音乐启蒙,让我对音乐的表现形式并不在意,却对内里表达异常敏感。反映到生活中,就是音乐器材上的低档次。
我仿佛已经看到ARTEC同学鄙视的笑我:你这个没品的东西!没办法,一个人的喜好如果形成了,很难改。好的器材我并不排斥,只是很多时候没钱而已,总觉得费效比不高。从无到有,总是让人非常惊喜的。而从60到100,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没有脱贫的感觉那么好。
想起了我儿时最好的伙伴,一台春雷牌收音机。父亲从新疆把它带回来了。想想当年在里面第一次听到李光羲《祝酒歌》的时候,真是惊喜啊,还有每天不能错过的《小喇叭》。可惜我的孩子是没有这种幸福了。只能让我给他讲故事了,嗯,要不要搞个小喇叭的开头曲,给他启蒙一下呢?
音乐习惯这种东西,还是有点传承的好。散场